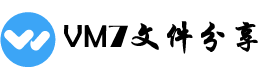暗蛾破繭的那個剎那
[导读]:傅丝宝在一个梦里惊醒。梦里她在与邱好做爱,淋漓欢畅,她满足地仰脸看他,从他的眼睛中看到双颊绯红的自己,幸福且性福的女人。邱好是立在床边的,她只能看到他结实瘦...
傅丝宝在一个梦里惊醒。梦里她在与邱好做爱,淋漓欢畅,她满足地仰脸看他,从他的眼睛中看到双颊绯红的自己,幸福且性福的女人。邱好是立在床边的,她只能看到他结实瘦削的上半身,只能触摸到他手臂上勃起的肌肉,坚实有力,每一寸肌肤都带着入侵性。她陶醉在被他入侵之中,在入侵中她徒劳地呻吟。如果梦在此刻醒来,便是两腿间的一团温湿,心里的一阵可供回味的暗悸,她可以娇羞地打通他的电话,告诉他,她在春之梦中思念着他。可是,梦真是无理,不按她追寻的美好形式结束,高潮不能让她醒来,她想醒也不能。
傅丝宝将被子拉过头顶,脸还是红的,不是因为春梦渡红了双颊,而是因为他的话——他,怎么可以在梦中说出那样的话?
他的表情比她还要痛苦,那句话仿佛在他心里已盘桓很久,像躲在茧中的蛾子,暗处的挣扎她看不见,但是破茧的一刹那,他解脱了,她吓着了。
邱好说:“你,为什么一直要假装高潮呢?”
傅丝宝在梦里木木地张着嘴,仿佛嘴里含着糖块,因为倒吸一口冷气,糖块冲进了她的咽喉,她感觉硬物在哽的不快,感觉窒息的痛苦,她说不出话,她在自己的沉默中醒来,遍身汗,羞忿的脸红心喘。
你,为什么一直要假装高潮?
你,傅丝宝,确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吗?
这两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让她连起床、穿衣、开车时都不能专注。
她的白色帕萨特在道路上行走得恍惚,交警将她拦下,她看着女交警暗黄平庸的脸,忽然想起电视里常播的那个广告——交警问驾车的女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样年轻吗?”她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她也有问题,与女人的皮肤一样揪心劳神的问题,属于女人自己的隐密问题。她想问:“能告诉我你与丈夫或男友的性生活可有高潮?能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吗?”她咬住自己的嘴唇,听任交警检查她的行车证与驾照,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害怕她一张嘴,那只蛾子便会飞出来,盘桓在她心暗处侍机破茧的蛾子。
交警提醒她注意车速,挥手放行。她慢慢地踩动油门,松开离合器,不肯换档,在汽车因低档高油门发出的呻吟中向公司方向开去。泊车时,她忽然想,对邱好而言,她的呻吟是否就是那低档高速时所以出的难耐的声音?是否他渴望换高档,那只需加一点点油门便能轻松提速的伴侣?
她开始怀念少年时的恋情,只管情,不顾性,生活便简单好多。
当她进公司时,正好看到广告创意人员向制作人员口沫横飞地讲创意,他挥着着手,由低向高的手势,他说:“创意的高潮便在这里……”
傅丝宝烦燥地闭闭眼,从他们身边经过,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将自己锁在一个听不见高潮的空间。
电话响。邱好的声音。
他习惯每天早晨上班时给她一个电话问候心情。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要天天想念却不要天天见面,要在同一个城市却不要有共同的房间。
有时候见面并不能让两颗心贴近,有些话只有在电话里才能说得坦然。
邱好觉察出傅丝宝的沮丧,温柔地垂询:“怎么了?上班的路上不顺心?”
那只蛾子又在咬茧了。她咬死自己的下唇,不想说话。
“丝宝!”
他的声音是削尖的铅笔,轻易便将茧捅破,蛾子从空隙中露头,她说:“你对我们的性事,可满意?”
邱好愣了一下,四下看看,一上班就和女友电话聊性,让他有些不安。
他局促地问:“你怎么会问这个?”
“你对我,满意吗?”
邱好仓促地笑,有些意外,感觉电话对方的女人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
傅丝宝一直是含蓄的女人。含蓄,甚至有些过份乖巧。他与她每每聊到性事,类如“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她都不肯直面回答,总是将头埋进他颈后,抱着他,不易觉察地“嗯”一声,随他去判断她给还是不给。性完后,她在他怀里,安静沉默,不似有的女人性后如经典回顾,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进球,都要回味评述。
含蓄的傅丝宝在电话那端追问:“你对我,满意吗?”
邱好却想到了与这个问题无关的情景。
那天,他逼问丝宝可有高潮。
丝宝脸红,将问题回推给他:“你不知道吗?”
“问你呢。”
她通红着脸,吃力地重重点了几下头表示回答。
邱好满足地笑,兴奋地追问她高潮来到时是什么感觉。
傅丝宝将脸藏进头发里,嗡声嗡气地说:“你看不出来吗?”
“不许反问我,我要听你说。”
“很快乐,浑身无力,颤抖,嗯……还有……我描述不出。”她讲话时的神情真是可怜,仿佛回答这样的问题还不如在她身上捅一刀来得轻松。
邱好有些忧虑,他想,傅丝宝真的知道什么是高潮吗?为什么她所描述的与别的女人向他描述的并不相同。他不敢将这个问题抛出,害怕刺伤她乖巧柔软的心脏,而且,她能否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对他并不是很重要。他能肯定她爱他,这便够了,关于性,早有流行歌曲唱出女人心声:“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你为什么不说话?”傅丝宝音调一变,锐器在玻璃上划过的声音。
他有些迷惘了,脑中忽然有个念头闪过——难道,她不满意他,或者是她发现了更能让她满意的男人。
念头一闪便牢牢抓住了他的脑。他想,一定是这样吧,她一向喜欢将问题推给对方,这次一定也不例外,所以她会喋喋追问他是否满意。
“喂,邱好!”傅丝宝有些急了。
“晚上我去你那儿,我们见面再说。”邱好匆忙收了线,倒不是仅是因为丝宝今天奇怪的问题让他不安,而是他忽然想到秘书有可能会在外面拿着分机偷听。
他看不见远处傅丝宝的表情,她拿着发出盲音的电话听筒,表情木讷。她在想:一定是这样了,他不满意,所以他难以回答。
女人一向善于联想,她开始想他与她迟迟不结婚也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和谐的性事,忘记了几个月前自己还在向他强调,如果她想要婚姻了,便是她想要一个孩子了,而现在公司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她专职生养。
白色的蜡烛,餐桌上放着外卖送来的热腾腾的铁盘比萨。傅丝宝已经洗过澡,不动声色地换上了新买的深紫色内衣。她不无伤感地看着白色蜡烛滴下的白色的烛泪。她想她真是失败,做女人这样久,还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这是最后的晚餐了,她要向过去告别,她要在今天寻找那一直被她忽略的感觉。
邱好感觉今天的傅丝宝很奇怪。当他解开她的外衣看到那一抹妖媚的紫色时,他的手迟疑了一下。她什么时候换了品味?穿米色胸围的傅丝宝才是傅丝宝,而这具穿紫色胸围的身体,她要么是属于另一个女人,要么便是属于另一个男人。
这样想,他居然激动起来。臆想给了他新鲜的刺激。
可是他不能持久。换了任何一个男人可能都不会持久——她的身体僵硬,表情怪异,眼睛闪着探索钻研的光。她不像是在做爱,而是做试验。关于身体机能探究的试验。
“丝宝,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他徒劳地坐在她身边,后背给她,不肯给她正面。
身后的女人不声响,空气中响着细碎的抽泣。他扭过头,看见她俯在枕头上哭。
“你对我不满意!”她用了陈述句语气。
这话在邱好听来便成了另一种含义,是她对他不满意,这次他的表现这样不好,所以她更有理由哭泣,更有理由不满意。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地穿衣。她一直在哭,哭声在他关上门的那一刹那变得尖锐凄利。
小小的争吵不足以毁灭根深叶庞的两人关系。他们还爱着对方。所以妥协就来得便捷容易。但是这次又与往次不同。一堵有过破裂的木板墙,不管他们在破裂处钉上多少钉子夯上多少木条,哪怕再在破损处挂上一幅风景画,都不能改变破裂本身。性原来是他们最无间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最大的障碍。他与她,在床上时都兢兢业业,处处小心地观察对方的感觉。
于是,她真的不再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叫高潮。她的呻吟越来越假,假得连自己都感觉炸耳。
于是,他真的在她身上得不到快乐,只有生理高潮,短暂的,转瞬即逝,接下来便是在她刻意呻吟声中无法自拨的沮丧。
他们越来越少在一起过夜。约会的时间改在中午,一起午餐,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边感谢不用经历让人难堪的性事,一边聊天。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感觉对方的存在,或是感觉自己存在于对方。
邱好有了新的女友,他知道他并不爱她,但是他喜欢与她做爱时的感觉。
傅丝宝在街边看到咖啡厅落地玻璃窗后亲昵的两人时,并没有感觉特别沮丧。该来的总是要来了。她这样想。淡定地走进咖啡厅。走到他们面前。自然地微笑,说了一声:“嗨!”
邱好呆住了。只有那女人,毫不知情,露出讨好的笑容。她以为傅丝宝是邱好的某个同事,她露出笑容的同时便下了决心要将傅丝宝拉拢。她要入侵邱好的生活,与他的每个朋友每个同事都交好。
“你吃晚饭了吗?”邱好这样说,脸色有些窘迫。
“吃过了。你放在我那儿的一些东西,什么时候拿走?”她问。
女人警觉起来。像只看到鸟落窗台的猫,表情忽然专注略带狰狞。
“拿走?”邱好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他没有想过与傅丝宝分手,傅丝宝已是他的一个习惯,虽然有些不舒服,却不能构成割舍的理由。
“你要是没有时间,让你女友去拿也行。”傅丝宝对女人露出善意的微笑。女人在她的笑容里读出了羡慕,她得意地看着邱好,感觉这样优秀的男人值得所有女人露出艳羡的表情。她不知道,傅丝宝羡慕的人是她,她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她一定能让邱好满足。
还是邱好自己去的傅丝宝家。
白色的蜡烛。餐桌上放着三文治。
以前的傅丝宝是一块比萨,馅在外面撒着,一目了然。现在的傅丝宝便是一块三文治了,各个角度看,内容都不一样。他读不懂她,更找不到与她沟通的桥梁。他除了无奈地看着她,听命她结束关系的安排,别无它法。
傅丝宝将他的牙刷睡衣等日常用品装进袋子里,在将袋子交给他的时候,她忽然失控了。她起初的平静不过是自欺的假象,她以为她能坦然接受,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他马上要从她的世界撤退,这个事实还是让她受不了。
她抱着自己哭。坐在餐桌边。头发垂在那三文治旁。
他想伸手去抱她。他有什么资格去抱她呢?他背叛了她,他被她赶出了自己世界的中心,他没有资格再去伸手。他犹豫着。手里的袋子簌簌地响。
最终,他叹着气,转身开门。
傅丝宝忽然站起来,红肿着眼睛抱住他的后背,她说:“你连多留一会儿也不肯?”
她在说什么?他疑惑地转回头。她的嘴唇扑了上来,不允许他去思考。
他们做爱了。这次她没有去想高潮这回事,她只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个念头让她像一只拧紧了的毛巾,绞成一团,不停滴水。他这次也没有去想她是否对他满意这回事,他只知道他以后无权碰她了。这个念头刺激得他像临上刑场的犯人,眼前的酒水要拼力饮光。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专注投入地做爱。
傅丝宝看见破茧的蛾在空中欢快地拍打翅膀。
性事之后。两人都瘫松着。湿了水的面条般。
他们第一次这样和谐,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和谐。
傅丝宝想: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高潮,他却要离开我了。
邱好想:我以前以为与丝宝永远不能有美好的性事真是愚蠢透顶。
傅丝宝想:如果他说不走,我会和他一起忘记那个女人。
邱好想:如果她让我留下,我不会走。
傅丝宝想:他还爱我吗?
邱好想:她还肯让我爱吗?
……
他们想了太多,多得以致于他们无暇开口。
这便是故事的全部了。
这其实也是男人与女人的全部,爱情的全部。
傅丝宝将被子拉过头顶,脸还是红的,不是因为春梦渡红了双颊,而是因为他的话——他,怎么可以在梦中说出那样的话?
他的表情比她还要痛苦,那句话仿佛在他心里已盘桓很久,像躲在茧中的蛾子,暗处的挣扎她看不见,但是破茧的一刹那,他解脱了,她吓着了。
邱好说:“你,为什么一直要假装高潮呢?”
傅丝宝在梦里木木地张着嘴,仿佛嘴里含着糖块,因为倒吸一口冷气,糖块冲进了她的咽喉,她感觉硬物在哽的不快,感觉窒息的痛苦,她说不出话,她在自己的沉默中醒来,遍身汗,羞忿的脸红心喘。
你,为什么一直要假装高潮?
你,傅丝宝,确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吗?
这两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让她连起床、穿衣、开车时都不能专注。
她的白色帕萨特在道路上行走得恍惚,交警将她拦下,她看着女交警暗黄平庸的脸,忽然想起电视里常播的那个广告——交警问驾车的女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样年轻吗?”她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她也有问题,与女人的皮肤一样揪心劳神的问题,属于女人自己的隐密问题。她想问:“能告诉我你与丈夫或男友的性生活可有高潮?能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吗?”她咬住自己的嘴唇,听任交警检查她的行车证与驾照,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害怕她一张嘴,那只蛾子便会飞出来,盘桓在她心暗处侍机破茧的蛾子。
交警提醒她注意车速,挥手放行。她慢慢地踩动油门,松开离合器,不肯换档,在汽车因低档高油门发出的呻吟中向公司方向开去。泊车时,她忽然想,对邱好而言,她的呻吟是否就是那低档高速时所以出的难耐的声音?是否他渴望换高档,那只需加一点点油门便能轻松提速的伴侣?
她开始怀念少年时的恋情,只管情,不顾性,生活便简单好多。
当她进公司时,正好看到广告创意人员向制作人员口沫横飞地讲创意,他挥着着手,由低向高的手势,他说:“创意的高潮便在这里……”
傅丝宝烦燥地闭闭眼,从他们身边经过,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将自己锁在一个听不见高潮的空间。
电话响。邱好的声音。
他习惯每天早晨上班时给她一个电话问候心情。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要天天想念却不要天天见面,要在同一个城市却不要有共同的房间。
有时候见面并不能让两颗心贴近,有些话只有在电话里才能说得坦然。
邱好觉察出傅丝宝的沮丧,温柔地垂询:“怎么了?上班的路上不顺心?”
那只蛾子又在咬茧了。她咬死自己的下唇,不想说话。
“丝宝!”
他的声音是削尖的铅笔,轻易便将茧捅破,蛾子从空隙中露头,她说:“你对我们的性事,可满意?”
邱好愣了一下,四下看看,一上班就和女友电话聊性,让他有些不安。
他局促地问:“你怎么会问这个?”
“你对我,满意吗?”
邱好仓促地笑,有些意外,感觉电话对方的女人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
傅丝宝一直是含蓄的女人。含蓄,甚至有些过份乖巧。他与她每每聊到性事,类如“要”还是“不要”的问题她都不肯直面回答,总是将头埋进他颈后,抱着他,不易觉察地“嗯”一声,随他去判断她给还是不给。性完后,她在他怀里,安静沉默,不似有的女人性后如经典回顾,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进球,都要回味评述。
含蓄的傅丝宝在电话那端追问:“你对我,满意吗?”
邱好却想到了与这个问题无关的情景。
那天,他逼问丝宝可有高潮。
丝宝脸红,将问题回推给他:“你不知道吗?”
“问你呢。”
她通红着脸,吃力地重重点了几下头表示回答。
邱好满足地笑,兴奋地追问她高潮来到时是什么感觉。
傅丝宝将脸藏进头发里,嗡声嗡气地说:“你看不出来吗?”
“不许反问我,我要听你说。”
“很快乐,浑身无力,颤抖,嗯……还有……我描述不出。”她讲话时的神情真是可怜,仿佛回答这样的问题还不如在她身上捅一刀来得轻松。
邱好有些忧虑,他想,傅丝宝真的知道什么是高潮吗?为什么她所描述的与别的女人向他描述的并不相同。他不敢将这个问题抛出,害怕刺伤她乖巧柔软的心脏,而且,她能否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对他并不是很重要。他能肯定她爱他,这便够了,关于性,早有流行歌曲唱出女人心声:“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你为什么不说话?”傅丝宝音调一变,锐器在玻璃上划过的声音。
他有些迷惘了,脑中忽然有个念头闪过——难道,她不满意他,或者是她发现了更能让她满意的男人。
念头一闪便牢牢抓住了他的脑。他想,一定是这样吧,她一向喜欢将问题推给对方,这次一定也不例外,所以她会喋喋追问他是否满意。
“喂,邱好!”傅丝宝有些急了。
“晚上我去你那儿,我们见面再说。”邱好匆忙收了线,倒不是仅是因为丝宝今天奇怪的问题让他不安,而是他忽然想到秘书有可能会在外面拿着分机偷听。
他看不见远处傅丝宝的表情,她拿着发出盲音的电话听筒,表情木讷。她在想:一定是这样了,他不满意,所以他难以回答。
女人一向善于联想,她开始想他与她迟迟不结婚也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和谐的性事,忘记了几个月前自己还在向他强调,如果她想要婚姻了,便是她想要一个孩子了,而现在公司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她专职生养。
白色的蜡烛,餐桌上放着外卖送来的热腾腾的铁盘比萨。傅丝宝已经洗过澡,不动声色地换上了新买的深紫色内衣。她不无伤感地看着白色蜡烛滴下的白色的烛泪。她想她真是失败,做女人这样久,还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高潮。这是最后的晚餐了,她要向过去告别,她要在今天寻找那一直被她忽略的感觉。
邱好感觉今天的傅丝宝很奇怪。当他解开她的外衣看到那一抹妖媚的紫色时,他的手迟疑了一下。她什么时候换了品味?穿米色胸围的傅丝宝才是傅丝宝,而这具穿紫色胸围的身体,她要么是属于另一个女人,要么便是属于另一个男人。
这样想,他居然激动起来。臆想给了他新鲜的刺激。
可是他不能持久。换了任何一个男人可能都不会持久——她的身体僵硬,表情怪异,眼睛闪着探索钻研的光。她不像是在做爱,而是做试验。关于身体机能探究的试验。
“丝宝,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他徒劳地坐在她身边,后背给她,不肯给她正面。
身后的女人不声响,空气中响着细碎的抽泣。他扭过头,看见她俯在枕头上哭。
“你对我不满意!”她用了陈述句语气。
这话在邱好听来便成了另一种含义,是她对他不满意,这次他的表现这样不好,所以她更有理由哭泣,更有理由不满意。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地穿衣。她一直在哭,哭声在他关上门的那一刹那变得尖锐凄利。
小小的争吵不足以毁灭根深叶庞的两人关系。他们还爱着对方。所以妥协就来得便捷容易。但是这次又与往次不同。一堵有过破裂的木板墙,不管他们在破裂处钉上多少钉子夯上多少木条,哪怕再在破损处挂上一幅风景画,都不能改变破裂本身。性原来是他们最无间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最大的障碍。他与她,在床上时都兢兢业业,处处小心地观察对方的感觉。
于是,她真的不再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叫高潮。她的呻吟越来越假,假得连自己都感觉炸耳。
于是,他真的在她身上得不到快乐,只有生理高潮,短暂的,转瞬即逝,接下来便是在她刻意呻吟声中无法自拨的沮丧。
他们越来越少在一起过夜。约会的时间改在中午,一起午餐,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边感谢不用经历让人难堪的性事,一边聊天。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感觉对方的存在,或是感觉自己存在于对方。
邱好有了新的女友,他知道他并不爱她,但是他喜欢与她做爱时的感觉。
傅丝宝在街边看到咖啡厅落地玻璃窗后亲昵的两人时,并没有感觉特别沮丧。该来的总是要来了。她这样想。淡定地走进咖啡厅。走到他们面前。自然地微笑,说了一声:“嗨!”
邱好呆住了。只有那女人,毫不知情,露出讨好的笑容。她以为傅丝宝是邱好的某个同事,她露出笑容的同时便下了决心要将傅丝宝拉拢。她要入侵邱好的生活,与他的每个朋友每个同事都交好。
“你吃晚饭了吗?”邱好这样说,脸色有些窘迫。
“吃过了。你放在我那儿的一些东西,什么时候拿走?”她问。
女人警觉起来。像只看到鸟落窗台的猫,表情忽然专注略带狰狞。
“拿走?”邱好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他没有想过与傅丝宝分手,傅丝宝已是他的一个习惯,虽然有些不舒服,却不能构成割舍的理由。
“你要是没有时间,让你女友去拿也行。”傅丝宝对女人露出善意的微笑。女人在她的笑容里读出了羡慕,她得意地看着邱好,感觉这样优秀的男人值得所有女人露出艳羡的表情。她不知道,傅丝宝羡慕的人是她,她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潮,她一定能让邱好满足。
还是邱好自己去的傅丝宝家。
白色的蜡烛。餐桌上放着三文治。
以前的傅丝宝是一块比萨,馅在外面撒着,一目了然。现在的傅丝宝便是一块三文治了,各个角度看,内容都不一样。他读不懂她,更找不到与她沟通的桥梁。他除了无奈地看着她,听命她结束关系的安排,别无它法。
傅丝宝将他的牙刷睡衣等日常用品装进袋子里,在将袋子交给他的时候,她忽然失控了。她起初的平静不过是自欺的假象,她以为她能坦然接受,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他马上要从她的世界撤退,这个事实还是让她受不了。
她抱着自己哭。坐在餐桌边。头发垂在那三文治旁。
他想伸手去抱她。他有什么资格去抱她呢?他背叛了她,他被她赶出了自己世界的中心,他没有资格再去伸手。他犹豫着。手里的袋子簌簌地响。
最终,他叹着气,转身开门。
傅丝宝忽然站起来,红肿着眼睛抱住他的后背,她说:“你连多留一会儿也不肯?”
她在说什么?他疑惑地转回头。她的嘴唇扑了上来,不允许他去思考。
他们做爱了。这次她没有去想高潮这回事,她只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个念头让她像一只拧紧了的毛巾,绞成一团,不停滴水。他这次也没有去想她是否对他满意这回事,他只知道他以后无权碰她了。这个念头刺激得他像临上刑场的犯人,眼前的酒水要拼力饮光。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专注投入地做爱。
傅丝宝看见破茧的蛾在空中欢快地拍打翅膀。
性事之后。两人都瘫松着。湿了水的面条般。
他们第一次这样和谐,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和谐。
傅丝宝想: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高潮,他却要离开我了。
邱好想:我以前以为与丝宝永远不能有美好的性事真是愚蠢透顶。
傅丝宝想:如果他说不走,我会和他一起忘记那个女人。
邱好想:如果她让我留下,我不会走。
傅丝宝想:他还爱我吗?
邱好想:她还肯让我爱吗?
……
他们想了太多,多得以致于他们无暇开口。
这便是故事的全部了。
这其实也是男人与女人的全部,爱情的全部。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微盟圈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vm7.com/a/ask/61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