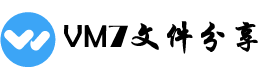孩子早戀的父母們應該讀的一篇美
[导读]:前言:现在“早恋”已经成为许多父母头痛的问题,束手无策。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早恋的美丽的文章,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我想如果父母看到后给自己的...
前言:现在“早恋”已经成为许多父母头痛的问题,束手无策。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早恋的美丽的文章,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我想如果父母看到后给自己的孩子看一下,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了,但孩子内心深处对于真挚的情感的感受还是一样的。
她可是冷了,初春的风实在有些刺骨,她使劲儿跺跺脚,下边是一片又湿又滑的柳眉儿。她又转过身,细细打量了一下身后的柳树。不错,说好是在这儿等的,池塘边这棵树干最粗,树皮最皴,枝条最高的柳树下面。可是,怎么他还没来呢?
塘里弥漫出一团雾气,稍远些,灌木丛啦、葡萄架啦、教学楼啦,什么都看不清,似乎一切都在雾中飘浮。
“我也在雾中飘浮。”她恍恍惚惚地想。是呀,那件事真让她头脑发晕。
是昨天中午,她在学校收到一封信。看信封上粗犷的笔迹,她就知道是他的。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写信干什么?她奇怪地想,同时心跳一下子加快了,觉到了什么。她跑到校园里的灌木丛中,拆开了信封。
雪白的信纸上,只有这两行字:
愿意与我永远同行吗?
等着你的回答。
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又读了好几遍,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她低下头,脸红了,一直红到颈项。什么话!她不禁有些愤怒,可是又有一丝甜蜜,一丝慌乱。唉!第一个大胆的人哪!
怎么办?拒绝还是答应?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她漫无目的地穿行着,摘了片树叶在手里揉着。
他是一个可敬不可亲的人,同学们都这样认为。棱角分明的骨骼,宽厚低沉的嗓音,透出一种威严和力量。各门学科的成绩都很好,下乡集中劳动的时候,谁也没他能干,可就是孤僻。
在一个班里呆了一年半,他们之间说的话不会超过五句。这学期,他的座位调到她的后面,他们才稍微有了些话。她说不清是哪一天,她采来许多的草茎,编了好些小猫、小狗,放在课桌上玩。他进来了,在她的课桌前停下脚步。“真有趣!”他说,眼里放出热诚的光,然后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不想念是她做的。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又轻轻地唤她的名字,请求给他一只小猫。她给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接触。以后之间的话多起来了。他常常问她正在看些什么书,有时会主动帮她借到;甚至她独自在为一道习题伤脑筋时,他也会悄悄地扔过来一张写着提示的小纸条;再以后,再以后……
不管她承不承认,她心里开始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愿望。她希望看到他,无论他是在皱着眉头啃书本,在黑板前演算习题,还是手拉着单杠做引体向上,低着头慢慢地散步,只要他在,哪怕她瞥见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她也觉得心里安稳些。那天晚上,他参加物理竞赛去了,结果两节自习课,她什么事儿也没做成,心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学习却渐渐比以前刻苦起来。每当她想马马虎虎地混过去时,心底就有一个声音响起:看他的成绩多好,他多有毅力,自己太差劲了,不行。
可是再怎么说,她也绝没想到他会这样直率地给她写信。她慌乱了,直到下午的上课铃响了,她也没想出该怎么办。
她低着头走进教室,凭直觉她能感到一种含着深深期待的目光,闪闪烁烁地经过她的脸。
上完课,他走过她身边时,她正好抬起头,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好像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竟然不由自主地说,明天早上五点,她在校园里池塘边老柳树下等他,那时再回答。
她的眼光迷茫地望着远方。天上的月儿淡了,星子隐了,天空呈现出灰白色。他该来了。她希望早点听到那熟悉的跫音,因为她实在累了,昨夜,感情与理智的斗争一直折磨着她,她几乎一点也没睡着呵!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跫音不要响起,因为昨夜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怎么能答应呢?她其实并没有很深地了解他啊!感情渴求着答应,然而理智的声音盖过了感情。可她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若是他也痛苦……
他其实早已来了。
站在离她不远的一棵树后面,看着她的背影,他反而犹豫了。他不住地按着口袋,好像再也鼓不起写信时的那股勇气了,他甚至后悔自己太冒失。如果她生气了,如果她以后再也不理自己,那多糟糕,那还不如不写那封信,而像过去一样地呆在一起的好。
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投出了那封信。然而这是真的。他觉得同她接触以前,自己浑浑噩噩,就像一团泥。只知道拼命地读书、解题,连跟同学多说句话,也认为是浪费时间。她的出现,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使他看到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色彩。
那天真冷,教室里没几个人。他埋头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不时冻得跺跺脚,哈哈手。她轻手轻脚进来了,手里捂着一只漂亮的玻璃热水瓶子。平时最爱大惊小怪的胖妞忙挨上去,借来暖暖手。她微笑着递上去。突然“砰”的一声,热水瓶子爆了。“哎哟!”胖妞惊叫起来。“活该!”他有点兴奋。而她却立刻跑到胖妞那儿,捧起胖妞的手连连问道:“疼吗?哪儿破了?”一点也不关心她那只漂亮瓶子的命运。“这儿,这儿疼,”胖妞撅起嘴来。他不禁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做作!”她却不那相想,她把眼睛靠近那只手,同情地说:“呀,有个口子呢!别动,还出血了,我帮你把脏血挤出来。”随后,就陪她去医务室了。教室的门轻轻关上了,他心里猛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天真冷,而自己的心不比天还冷吗?
随着与她的接触,他发觉自己的感觉渐渐变得敏锐了。雨后的大树,阳光下的草地,微风中的泥土味,还有那舒展的云,辉煌的落日……所有这一切都深深震动着他,使他感到有种不可言传的美。周末回家,他注意到母亲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鬓边又多了几根白发,立刻,他的心缩紧了,他真想为母亲拢一拢头发,并轻轻地拥抱一下瘦小的母亲。同学病了,他会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跑到市中心去买营养品,去耐心地安慰同学,陪着同学聊天。他的心中洋溢着温情。
他明白自己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全是因为有了她。她是他的阳光,他的空气。他要永远永远和她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护着她,使她快乐、幸福。
就在这温馨的傍晚,他伏在教室的窗台上,凝视着遥远的夕阳,这时,她的身影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提笔写下了那封信。
心灵的处罚来了。现在他是那样慌乱,从来没有过的慌乱。他反复地想,如果她要是拒绝了,留给自己的将是永远的悔恨,自己的痛苦倒尚在其次,若从此给她留下一丝阴影,那怎么能原谅自己呢?如果答应……自己是否有力量保护她,对她负责?
他看见她使劲地跺脚,两肩微微瑟缩着。是呀,自己也觉得冷了,那样一个女孩子,能不冷吗?他按了按口袋,暗暗下定了决心不能让她再等了!上前去,什么也不要想。
她确实等急了,她甚至担心是不是他出事了。从池塘上收回目光,她又低下头去。咦,浅绿色的柳眉儿上,多了一双穿着球鞋的脚,鞋帮湿了,上面尽是泥。她明白他是来了,这“坏蛋”什么时候到的?
“来啦?”她招呼着,嘴唇动了动,并没有转过身去。
“嗯。”他只是动了动嘴唇。
沉默。他的心里乱极了,接下来怎么办?
慢慢地,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只小小的纸船儿。“我们让小船儿航行,好不好?”他轻轻地说,同时摘了一片草叶放在一只船里,摘了一朵花放在另一只船里。
她疑惑地望着他,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他蹲在池塘边,又掐了根长长的草茎,也没转过身,似乎不经意地在说:“你愿意让这两只小船儿同行吗?”
她一下子愣住了,可马上便明白过来,心里有点感激他。她想拒绝,可嘴巴刚要张开,又闭紧了。她看见他回过头来,眼睛异常清亮,满含着真诚的期待。她犹豫了,甚至想俯下身去理理他的湿发。
她没有开口,也没有动,只是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池塘。池塘上仍然弥漫着雾气,只是比先前淡了。浅绿色的柳眉儿在眼前飘过。
“你,不愿意吗?”他有些迟疑,音调异常柔和。
“不愿意。”她说,自己也不清楚是怎样发出这三个字音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她低下头,抚弄着那根柳枝。一片柳眉儿落在她的头上。
“真的不愿意?”他又问,并转过身去。
“不愿意。”她说,同时扭过头,心里觉得有一丝苦涩。
他没再说话,只是站起身,把放了花儿的小船放在她的左手心里,凝视了小船一眼,便转过身走了,脚步轻轻的。
“啪嗒!”她手中的柳枝断了。他停下了脚步。
“听着,”她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大声说,“我不拒绝!”
他转过身,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走过来,从她手心上取过那只小船儿。
她没有拒绝,但却忧郁地别过头去。“我不拒绝,可也不愿意。这两只小船儿太小了,可不是?还没下过水呢!它们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吗?它们能知道对方的目标并且永远行驶在一条航道上吗?”
他的手垂了下去,纸船儿滑到地上。
“它们现在互相喜欢着,不错,可仅仅喜欢是不够的。”
她继续缓缓地说,“如果有一天,它们猛然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同行者并不是对方,那时又该怎么办?”
她的声音仿佛在池塘上飘,他思索着。
他说话的速度猛然加快了:“给我五年的时间,等到五年以后,我也许就能明确地回答你了。”
“不,不好!”她想了一想,又摇摇头,“最好是现在就让小船儿在水中自由地漂,忘掉你的问题。也许五年以后,它们会重新相遇,并沿着同一条航线前行,也许……”她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也许用不了五年,它们就会离得远远的,永远不再想起对方。”
“不会,我想念至少有一只小船儿不会。”他认真地说,就像是宣布一道几何定理似的。
“等着瞧吧。”她狡黠地一笑,真笑了。
“该让船儿启航了!”他提醒她。
于是他们蹲下,郑重地把小船儿放进了水里。然后又一同站起来,很快地转身,不再看那小船儿。
一只小手伸了出来。
一只大手伸了出来。
小手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她可是冷了,初春的风实在有些刺骨,她使劲儿跺跺脚,下边是一片又湿又滑的柳眉儿。她又转过身,细细打量了一下身后的柳树。不错,说好是在这儿等的,池塘边这棵树干最粗,树皮最皴,枝条最高的柳树下面。可是,怎么他还没来呢?
塘里弥漫出一团雾气,稍远些,灌木丛啦、葡萄架啦、教学楼啦,什么都看不清,似乎一切都在雾中飘浮。
“我也在雾中飘浮。”她恍恍惚惚地想。是呀,那件事真让她头脑发晕。
是昨天中午,她在学校收到一封信。看信封上粗犷的笔迹,她就知道是他的。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写信干什么?她奇怪地想,同时心跳一下子加快了,觉到了什么。她跑到校园里的灌木丛中,拆开了信封。
雪白的信纸上,只有这两行字:
愿意与我永远同行吗?
等着你的回答。
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又读了好几遍,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她低下头,脸红了,一直红到颈项。什么话!她不禁有些愤怒,可是又有一丝甜蜜,一丝慌乱。唉!第一个大胆的人哪!
怎么办?拒绝还是答应?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她漫无目的地穿行着,摘了片树叶在手里揉着。
他是一个可敬不可亲的人,同学们都这样认为。棱角分明的骨骼,宽厚低沉的嗓音,透出一种威严和力量。各门学科的成绩都很好,下乡集中劳动的时候,谁也没他能干,可就是孤僻。
在一个班里呆了一年半,他们之间说的话不会超过五句。这学期,他的座位调到她的后面,他们才稍微有了些话。她说不清是哪一天,她采来许多的草茎,编了好些小猫、小狗,放在课桌上玩。他进来了,在她的课桌前停下脚步。“真有趣!”他说,眼里放出热诚的光,然后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不想念是她做的。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又轻轻地唤她的名字,请求给他一只小猫。她给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接触。以后之间的话多起来了。他常常问她正在看些什么书,有时会主动帮她借到;甚至她独自在为一道习题伤脑筋时,他也会悄悄地扔过来一张写着提示的小纸条;再以后,再以后……
不管她承不承认,她心里开始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愿望。她希望看到他,无论他是在皱着眉头啃书本,在黑板前演算习题,还是手拉着单杠做引体向上,低着头慢慢地散步,只要他在,哪怕她瞥见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她也觉得心里安稳些。那天晚上,他参加物理竞赛去了,结果两节自习课,她什么事儿也没做成,心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学习却渐渐比以前刻苦起来。每当她想马马虎虎地混过去时,心底就有一个声音响起:看他的成绩多好,他多有毅力,自己太差劲了,不行。
可是再怎么说,她也绝没想到他会这样直率地给她写信。她慌乱了,直到下午的上课铃响了,她也没想出该怎么办。
她低着头走进教室,凭直觉她能感到一种含着深深期待的目光,闪闪烁烁地经过她的脸。
上完课,他走过她身边时,她正好抬起头,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好像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竟然不由自主地说,明天早上五点,她在校园里池塘边老柳树下等他,那时再回答。
她的眼光迷茫地望着远方。天上的月儿淡了,星子隐了,天空呈现出灰白色。他该来了。她希望早点听到那熟悉的跫音,因为她实在累了,昨夜,感情与理智的斗争一直折磨着她,她几乎一点也没睡着呵!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跫音不要响起,因为昨夜思考的结果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拒绝,怎么能答应呢?她其实并没有很深地了解他啊!感情渴求着答应,然而理智的声音盖过了感情。可她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若是他也痛苦……
他其实早已来了。
站在离她不远的一棵树后面,看着她的背影,他反而犹豫了。他不住地按着口袋,好像再也鼓不起写信时的那股勇气了,他甚至后悔自己太冒失。如果她生气了,如果她以后再也不理自己,那多糟糕,那还不如不写那封信,而像过去一样地呆在一起的好。
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投出了那封信。然而这是真的。他觉得同她接触以前,自己浑浑噩噩,就像一团泥。只知道拼命地读书、解题,连跟同学多说句话,也认为是浪费时间。她的出现,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使他看到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色彩。
那天真冷,教室里没几个人。他埋头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不时冻得跺跺脚,哈哈手。她轻手轻脚进来了,手里捂着一只漂亮的玻璃热水瓶子。平时最爱大惊小怪的胖妞忙挨上去,借来暖暖手。她微笑着递上去。突然“砰”的一声,热水瓶子爆了。“哎哟!”胖妞惊叫起来。“活该!”他有点兴奋。而她却立刻跑到胖妞那儿,捧起胖妞的手连连问道:“疼吗?哪儿破了?”一点也不关心她那只漂亮瓶子的命运。“这儿,这儿疼,”胖妞撅起嘴来。他不禁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做作!”她却不那相想,她把眼睛靠近那只手,同情地说:“呀,有个口子呢!别动,还出血了,我帮你把脏血挤出来。”随后,就陪她去医务室了。教室的门轻轻关上了,他心里猛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天真冷,而自己的心不比天还冷吗?
随着与她的接触,他发觉自己的感觉渐渐变得敏锐了。雨后的大树,阳光下的草地,微风中的泥土味,还有那舒展的云,辉煌的落日……所有这一切都深深震动着他,使他感到有种不可言传的美。周末回家,他注意到母亲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鬓边又多了几根白发,立刻,他的心缩紧了,他真想为母亲拢一拢头发,并轻轻地拥抱一下瘦小的母亲。同学病了,他会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跑到市中心去买营养品,去耐心地安慰同学,陪着同学聊天。他的心中洋溢着温情。
他明白自己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全是因为有了她。她是他的阳光,他的空气。他要永远永远和她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护着她,使她快乐、幸福。
就在这温馨的傍晚,他伏在教室的窗台上,凝视着遥远的夕阳,这时,她的身影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提笔写下了那封信。
心灵的处罚来了。现在他是那样慌乱,从来没有过的慌乱。他反复地想,如果她要是拒绝了,留给自己的将是永远的悔恨,自己的痛苦倒尚在其次,若从此给她留下一丝阴影,那怎么能原谅自己呢?如果答应……自己是否有力量保护她,对她负责?
他看见她使劲地跺脚,两肩微微瑟缩着。是呀,自己也觉得冷了,那样一个女孩子,能不冷吗?他按了按口袋,暗暗下定了决心不能让她再等了!上前去,什么也不要想。
她确实等急了,她甚至担心是不是他出事了。从池塘上收回目光,她又低下头去。咦,浅绿色的柳眉儿上,多了一双穿着球鞋的脚,鞋帮湿了,上面尽是泥。她明白他是来了,这“坏蛋”什么时候到的?
“来啦?”她招呼着,嘴唇动了动,并没有转过身去。
“嗯。”他只是动了动嘴唇。
沉默。他的心里乱极了,接下来怎么办?
慢慢地,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只小小的纸船儿。“我们让小船儿航行,好不好?”他轻轻地说,同时摘了一片草叶放在一只船里,摘了一朵花放在另一只船里。
她疑惑地望着他,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他蹲在池塘边,又掐了根长长的草茎,也没转过身,似乎不经意地在说:“你愿意让这两只小船儿同行吗?”
她一下子愣住了,可马上便明白过来,心里有点感激他。她想拒绝,可嘴巴刚要张开,又闭紧了。她看见他回过头来,眼睛异常清亮,满含着真诚的期待。她犹豫了,甚至想俯下身去理理他的湿发。
她没有开口,也没有动,只是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池塘。池塘上仍然弥漫着雾气,只是比先前淡了。浅绿色的柳眉儿在眼前飘过。
“你,不愿意吗?”他有些迟疑,音调异常柔和。
“不愿意。”她说,自己也不清楚是怎样发出这三个字音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她低下头,抚弄着那根柳枝。一片柳眉儿落在她的头上。
“真的不愿意?”他又问,并转过身去。
“不愿意。”她说,同时扭过头,心里觉得有一丝苦涩。
他没再说话,只是站起身,把放了花儿的小船放在她的左手心里,凝视了小船一眼,便转过身走了,脚步轻轻的。
“啪嗒!”她手中的柳枝断了。他停下了脚步。
“听着,”她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大声说,“我不拒绝!”
他转过身,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走过来,从她手心上取过那只小船儿。
她没有拒绝,但却忧郁地别过头去。“我不拒绝,可也不愿意。这两只小船儿太小了,可不是?还没下过水呢!它们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吗?它们能知道对方的目标并且永远行驶在一条航道上吗?”
他的手垂了下去,纸船儿滑到地上。
“它们现在互相喜欢着,不错,可仅仅喜欢是不够的。”
她继续缓缓地说,“如果有一天,它们猛然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同行者并不是对方,那时又该怎么办?”
她的声音仿佛在池塘上飘,他思索着。
他说话的速度猛然加快了:“给我五年的时间,等到五年以后,我也许就能明确地回答你了。”
“不,不好!”她想了一想,又摇摇头,“最好是现在就让小船儿在水中自由地漂,忘掉你的问题。也许五年以后,它们会重新相遇,并沿着同一条航线前行,也许……”她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也许用不了五年,它们就会离得远远的,永远不再想起对方。”
“不会,我想念至少有一只小船儿不会。”他认真地说,就像是宣布一道几何定理似的。
“等着瞧吧。”她狡黠地一笑,真笑了。
“该让船儿启航了!”他提醒她。
于是他们蹲下,郑重地把小船儿放进了水里。然后又一同站起来,很快地转身,不再看那小船儿。
一只小手伸了出来。
一只大手伸了出来。
小手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微盟圈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vm7.com/a/ask/63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