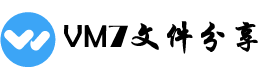汪國真是假詩人嗎?
[导读]:纪念刚刚离世的著名诗人汪国真的各种活动尚未止歇,学界、坊间围绕着他及其诗歌的争议,又开始骤然升起,仿佛多年前曾经的那样。 某个诗界地位很高的前辈曾论定汪国真是...
纪念刚刚离世的著名诗人汪国真的各种活动尚未止歇,学界、坊间围绕着他及其诗歌的争议,又开始骤然升起,仿佛多年前曾经的那样。
某个诗界地位很高的前辈曾论定汪国真是“假诗人”,汪诗是“假诗”。而某著名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在接受一个主流媒体采访时,也用似乎颇具权威的口吻说:“优秀的诗人好比概念车,其意义在于探索方向,挑战极限,如果说没有这种探索,后面的量产车就做不下去。汪国真在诗人中所处的位置,显然不是概念车,而是随后跟进的量产汽车。”
对这两种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先说前者,要评论某人是真诗人还是假诗人、其诗是真诗还是假诗,必须得有一套严格规范的、公认的、可参照执行的统一标准,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科学而非文化艺术范畴了。语言是文化的基石,诗歌又是语言中最精炼、升华的表现形式,诗人只能用境界高低、诗歌只能用优劣和雅俗等来衡量,不能用真假来划分对立。此为其一。
其二,如果该诗界前辈认定汪诗是假诗,那么笔者是否也可以顺其歪理,得出一个同样荒唐的结论:和笔者相比,你们写新诗的都是假诗人,我才是真正的“真诗人”。因为我能填制格律诗词,作品经常被人当作古人的诗句拿去写书法,而你们这些当代诗人都已“进化”或“退化”到只能写白话诗了。从诗经开始,如果站在两千多年不断的中国诗脉这一大背景下,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世界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美学等等的影响力,中国新文化运动后的这些新诗都无法和古代诗歌相媲美。
某种意义上说,宋人就是因其格律诗已无法超越唐人境界,所以才在格律词上独步天香,而元人的格律诗词都干不过唐宋之人,所以才在散曲杂剧上大放异彩,到了明清这两代又次之了,只好再白话一点、再通俗一些,把小说什么的演绎得叹为观止。顺着这种逻辑捋下来,是否可以说今人在哪种诗体上都拼不过古圣先贤,但又必须得“诗兴大发”,只好把白话文分行而成诗了呢?如果把我们和古人拉到同一时空里,还指不定谁把谁看成假诗人呢。
再说那位院长对汪诗的评论。在当下整个文化艺术缺乏正确定位和厘正的大背景下,就如同佛学一代代传下来,似乎已经渐渐忘却了2500多年前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那一瞬间的开悟本意一样;亦如同茶也变成了茶文化茶境界和茶价格被疯吹得满虚空里飞、而忘记茶本质是个农产品一样,现在中国的诗界被操盘得似乎也忘记了本来面目了。
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大序》),“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沧浪《诗话》)。所以诗歌大体上包含如下几个特点:抒情言志、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炼而具有音乐美、高度概括地反映生活等等。但是在某些诗人和评论家的筹划里当代新诗变成了一个工具,他们好像更关心自己属于哪一个派、哪一代。这一派玩不转了,就去玩另一派;这一代混不下去了,就赶紧创新另类概念,跳到下一代。其实,无论是量产车还是概念车,都请不要忘了车本身的概念,它只是一种安全实用舒适的代步、运输工具而已。要知道有多少概念车最终就生产了那么一台,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被历史淘汰了吗?
我也读过汪诗,不认为他是“假诗人”、他的诗是“假诗”;也不认同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划派论代、为概念而概念、为创新而创新的工具,从而忘了诗歌动心、感人、抒情、言志等本来面目。那种已经没有能力和天分来感动人心,退化到创新一些所谓的概念诗在圈里互相吹捧的诗人,才是真正的“假诗人”。
汪诗不能用真假来论定,但却可用优劣高下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的诗走大众通俗路线,可能过于直白,不够蕴藉。
那么什么诗才是比较优等的好诗呢?季羡林曾专门论述过,他援引在世界上独成体系的印度文艺理论来界定词汇的三重功能和意义,一:表示功能(字面义,本义);二:指示功能(引申义,转义);三:暗示功能(领会义)。以上又可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没有说出来的(第三种)。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这种暗示就是古印度人所谓的“韵”。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大、就越容易感到审美客体之美,这便是韵的奇妙作用,而韵是诗歌的灵魂。
故印度人以此来把诗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即暗示的东西为主(领会义);第二为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为了装饰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引申义,转义);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字面义,本义)。这和中国古人特指好诗的多重意境(重意)说如出一辙。
如古诗十九首里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共有有三重意境,第一:句中的本意;第二:文外之意,“浮云之蔽白日,以喻奸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文选》李善);第三:“当人之皎皎如白日的本心被世俗之风尘、云翳所遮蔽的时候,人就不能返本归真了”(《佛教与美学》)。
谨以此文纪念曾感动过无数人的汪国真诗人。
某个诗界地位很高的前辈曾论定汪国真是“假诗人”,汪诗是“假诗”。而某著名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在接受一个主流媒体采访时,也用似乎颇具权威的口吻说:“优秀的诗人好比概念车,其意义在于探索方向,挑战极限,如果说没有这种探索,后面的量产车就做不下去。汪国真在诗人中所处的位置,显然不是概念车,而是随后跟进的量产汽车。”
对这两种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先说前者,要评论某人是真诗人还是假诗人、其诗是真诗还是假诗,必须得有一套严格规范的、公认的、可参照执行的统一标准,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科学而非文化艺术范畴了。语言是文化的基石,诗歌又是语言中最精炼、升华的表现形式,诗人只能用境界高低、诗歌只能用优劣和雅俗等来衡量,不能用真假来划分对立。此为其一。
其二,如果该诗界前辈认定汪诗是假诗,那么笔者是否也可以顺其歪理,得出一个同样荒唐的结论:和笔者相比,你们写新诗的都是假诗人,我才是真正的“真诗人”。因为我能填制格律诗词,作品经常被人当作古人的诗句拿去写书法,而你们这些当代诗人都已“进化”或“退化”到只能写白话诗了。从诗经开始,如果站在两千多年不断的中国诗脉这一大背景下,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世界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美学等等的影响力,中国新文化运动后的这些新诗都无法和古代诗歌相媲美。
某种意义上说,宋人就是因其格律诗已无法超越唐人境界,所以才在格律词上独步天香,而元人的格律诗词都干不过唐宋之人,所以才在散曲杂剧上大放异彩,到了明清这两代又次之了,只好再白话一点、再通俗一些,把小说什么的演绎得叹为观止。顺着这种逻辑捋下来,是否可以说今人在哪种诗体上都拼不过古圣先贤,但又必须得“诗兴大发”,只好把白话文分行而成诗了呢?如果把我们和古人拉到同一时空里,还指不定谁把谁看成假诗人呢。
再说那位院长对汪诗的评论。在当下整个文化艺术缺乏正确定位和厘正的大背景下,就如同佛学一代代传下来,似乎已经渐渐忘却了2500多年前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那一瞬间的开悟本意一样;亦如同茶也变成了茶文化茶境界和茶价格被疯吹得满虚空里飞、而忘记茶本质是个农产品一样,现在中国的诗界被操盘得似乎也忘记了本来面目了。
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大序》),“诗者,吟咏性情也”(宋严沧浪《诗话》)。所以诗歌大体上包含如下几个特点:抒情言志、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炼而具有音乐美、高度概括地反映生活等等。但是在某些诗人和评论家的筹划里当代新诗变成了一个工具,他们好像更关心自己属于哪一个派、哪一代。这一派玩不转了,就去玩另一派;这一代混不下去了,就赶紧创新另类概念,跳到下一代。其实,无论是量产车还是概念车,都请不要忘了车本身的概念,它只是一种安全实用舒适的代步、运输工具而已。要知道有多少概念车最终就生产了那么一台,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被历史淘汰了吗?
我也读过汪诗,不认为他是“假诗人”、他的诗是“假诗”;也不认同仅仅把诗歌作为一种划派论代、为概念而概念、为创新而创新的工具,从而忘了诗歌动心、感人、抒情、言志等本来面目。那种已经没有能力和天分来感动人心,退化到创新一些所谓的概念诗在圈里互相吹捧的诗人,才是真正的“假诗人”。
汪诗不能用真假来论定,但却可用优劣高下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的诗走大众通俗路线,可能过于直白,不够蕴藉。
那么什么诗才是比较优等的好诗呢?季羡林曾专门论述过,他援引在世界上独成体系的印度文艺理论来界定词汇的三重功能和意义,一:表示功能(字面义,本义);二:指示功能(引申义,转义);三:暗示功能(领会义)。以上又可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没有说出来的(第三种)。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这种暗示就是古印度人所谓的“韵”。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大、就越容易感到审美客体之美,这便是韵的奇妙作用,而韵是诗歌的灵魂。
故印度人以此来把诗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即暗示的东西为主(领会义);第二为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为了装饰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引申义,转义);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字面义,本义)。这和中国古人特指好诗的多重意境(重意)说如出一辙。
如古诗十九首里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共有有三重意境,第一:句中的本意;第二:文外之意,“浮云之蔽白日,以喻奸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文选》李善);第三:“当人之皎皎如白日的本心被世俗之风尘、云翳所遮蔽的时候,人就不能返本归真了”(《佛教与美学》)。
谨以此文纪念曾感动过无数人的汪国真诗人。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微盟圈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vm7.com/a/ask/6603.html